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潘凯雄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开始有了“大”“小”年之分。有意味的是,这种“大”“小”之别,既不是由作品数量所定,也不是因作品质量而论。所谓“小”,指的是在“茅盾文学奖”评奖年,因获奖作品风头甚劲,于是相关人员遂心照不宣地将一些还不错的长篇小说避开这强劲的风头后再安排出版;除此之外的年份自然就谓之为“大”了。
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的这种“大”“小”年之别,其长则足以显示“茅奖”威风之威,其短或许也见出“茅奖”外的某种自信与不足。
姑且不论这种“大”“小”之分的长长短短,太招人。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状况在近些年正在逐渐被淡化、被消解。于文坛、于读者,这绝对是好事、幸事、正常事。
一
去年以来,我看过五位先后荣膺过“茅奖”的著名作家不约而同拿出的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这当然是一种巧合,但也确不是年年都能遇到。不妨一一简单道来。
《欢迎来到人间》是毕飞宇获得“茅奖”12年后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首度亮相。他过往的创作一般都被认为写得很精致,特别注重细节。包括上一部获“茅奖”的《推拿》就是如此。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以大夫为主角、以医疗为题材。在这部新长篇中,毕飞宇一如既往地保留了过往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极为细腻的一面,同时又新增了过往创作中不多见的十分粗粝而遒劲的笔墨。
而尤为重要的是,这部新作直接进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关注人的精神健康。对毕飞宇而言,这是他创作中的第一次。
看得出,他这一步走得虽很艰难但又十分坚定,这或许也是他继《推拿》面世长达12年之后才终于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缘由。作品中有些很荒诞的、读者或许觉得不尽合理的情节或细节,但我觉得这无疑是作家的故意为之。他就是想通过一些极端的艺术处理来传递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以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思考。这些个环节不能简单地以现实主义为法则、从现实生活的角度一一进行比对。迈出这一步,对毕飞宇而言,需要勇气和自信,但他还是决绝地迈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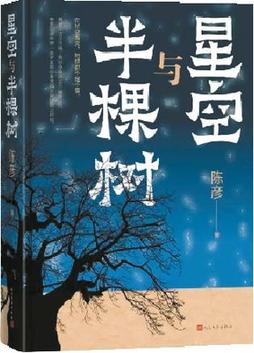
《星空与半棵树》陈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同样出手不凡。作者长期在戏剧领域工作,过往创作的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喜剧》等大抵都是表现他所熟悉的这个领域,也深受读者喜爱。而到了这部《星空与半棵树》,既有“半棵树”这个很小很小的入口,又有“星空”这样一个充满神奇与变幻的广阔世界,过去自己曾经熟悉的领域被拓展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依旧保留了十分精致与细腻的细节。作家这种主动的自我拓展显而易见。
长期被认为是写反腐题材第一人的张平有点久违了。千年之交前后,出自他手笔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和《国家干部》等都是在这一领域的重磅之作。后因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而不得不一度辍笔,新作《换届》则是他退出领导工作岗位重返文坛后的一部新长篇。依旧是反腐题材,但鲜有了以往作品中的那些个血乎刺拉,整个调子看上去较以往温和了不少。
作品题为《换届》,正是抓住了当下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与敏感的节点。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新的词叫“躺平”,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作为、懒政。而《换届》最大的特点与亮点,就是把当下社会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现实的大毒瘤很平静地予以呈现出来。这既是反腐小说的一种与时俱进,也是张平创作这类题材作品时政治敏感性的一贯风范。
贾平凹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劳模,啥得奖与否、大年小年,似乎都与他无关。在他那里,始终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每两年左右完成一部新长篇,《河山传》当是迄今为止他创作的第22或23部长篇了吧?
这部《河山传》在他全部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也算是十分特别的了。这个命名颇有点大气磅礴之势,但切口却不大。作品围绕着一个名为“河”的乡里娃子进城,和一个由乡下进城后已“混”成了看上去有头有脸的老板“山”说开去,《河山传》其名就是以这两人之名而来。
与平凹以往作品不同的是,虽依旧是乡下人进城,但《河山传》所呈现的却是一个大时代,折射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将这种变化通过两个曾经的农民进城后之生活历程展现出来。这样一种全景式的铺陈,的确也是贾平凹过往创作中不多见的。
还有格非的新长篇《登春台》。这是一部关乎对当代人欲望情感、彼此关联、时间危机和生存境遇等诸要素的作品,它以近40余年时光为背景,来自江南笤溪村、北京小羊坊村、甘肃地坑院洞穴和里下河平原小村庄的四位老少男女在北京春台路67号有了命运的交集。

《登春台》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读《登春台》,令人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个以“先锋作家”姿态出现于文坛的追风青年作家格非在小说叙事结构上所下过的功夫。比之于作品中那四位人物的命运起伏,格非这次在结构上似乎倾注了更多的心思。他们的故事在《登春台》这个平台上彼此镶嵌,而每个故事自身的指向及寓意依然清晰可见。
对此,格非自己的解释是:
“我现在认为文学是我在思考生活时的主要媒介。写作并不是说把思考定型的东西写入作品,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因为只有在写作时,那些你原先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才会一点点地从黑暗中呈现出来。”
“简单来说,我在想,能不能把四个不同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让各部分彼此镶嵌在一起,同时不去破坏每个故事自身的明晰性。”
在这里,作家自身的创作意图显然已经交代得一览无余,看上去有点复杂、有点烧脑,但我们在阅读这部不过20余万字的长篇新作时,依然清晰地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人物的命运,以及城乡边界的模糊等丰满鲜活的内容扑面而来。这种阅读效果的获取,得益于作家统筹处理丰满内容与叙事艺术关系的本事与能力。
上述五位曾经的“茅奖”获得者“不约而同”地奉献出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这当然只是一种偶然与巧合;但从本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这些新作又还有另一种“不约而同”。那就是“茅奖”于他们而言都不过只是过去的经历与记忆,而这些个新作所呈现出的主旨与面貌,和他们斩获“茅奖”的作品的确“相距甚远”。
这显然是作家们的刻意为之,既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更是他们创作自信的一种体现。
二
其实,近年来不只是曾经的“茅奖”作家新作纷呈,于扎实的艺术功底中见出不懈的艺术追求,还有更多中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新作纷纷面世,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瑰丽景观中尽显各自风采,凸显集体自信。

《平乐县志》颜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张楚和颜歌,这一北一南、一男一女的两位青年作家,去年各自完成了以县域为主场景的长篇小说新作。《云落图》着眼于北方县城,《平乐县志》则面向南方县域。我们常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现在这两位作家妙笔生花,将一南一北两个县城的当下生活给描绘得活色生香、烟火四溢。两位作家的叙事调性不同,置于一起比对着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阅读享受。
年轻女作家阿舍以新疆建设兵团数十年风雨历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也颇有特色。这不是一个令人完全陌生的领域,我们曾经读到过这里的一派“莺歌燕舞”,也看到过此地的“狂风暴雨”。而到了这部《阿娜河畔》,作者则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冷静的笔触,呈现那块热土上数十年的风雨沧桑:有热血、有发展;有疯狂、也有残酷,不回避不夸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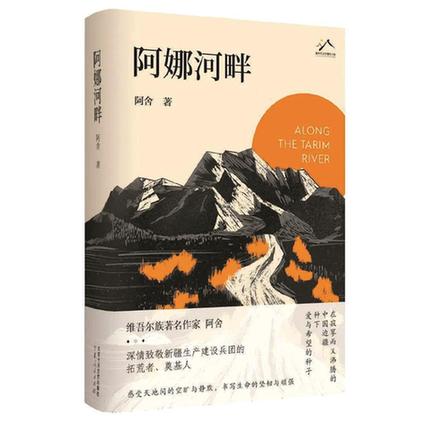
《阿娜河畔》阿舍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无论大气候如何,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暖意,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与成熟始终贯穿于《阿娜河畔》中。阿舍用一种十分平和、安静的叙事调性努力还原着那一个跌宕的特定时代。
张者的《万桥赋》当属主题性长篇小说写作。作者以贵州省的桥梁建设为媒来突显脱贫攻坚的主题,其实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的一种选项。作为全国最后一个全面脱贫的省份,贵州的桥梁建设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赢得了“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的美誉。如何将这个由钢筋混凝土为主体的庞大家伙转化为突显文学主题的载体?其难度其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张者借助于一个桥梁设计世家后代中最不爱桥者的蜕变巧妙地完成了这种转化,从而使得作品的主题在精巧的文学叙事中艺术性地得以突显。
三
去年以来陆续与读者见面且个性突出、特色鲜明、自信满满的长篇小说,当然不止于以上概括点评到的九位作家与作品。为控制本文的篇幅,下面不妨以一句话评述的方式再陈列10部新近面世的长篇小说新作。
——老藤的《北爱》,巧妙地将艺术与科技、商业与人文融于一体,书写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生以及大国重器背后的精神伟力。
——鬼子历时18年成就的《买话》,讲述了一个自认为无法融入城市却又回不去乡村的悲摧故事,城乡人际交往中的那种不可言说又不言自明的瞬间意味深长。
——须一瓜的《窒息的家·宣木瓜别墅》,围绕家庭及其间的人物关系展开,意在探讨家庭教育的模式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艾玛的《观相山》,尽写凡人琐碎生活,看似平淡与乏味中巧妙见出人生与人性的真切与丰盈。
——李清源的《窑变》,创造性地将“窑变”作为人世变迁的隐喻,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的笔触,在钧瓷复烧中刻写“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人生哲理。
——肖勤的《血液科医生》,一面将人性中的种种不堪与丑陋无情地暴露于阳光之下,另一方面更是在大力张扬人性中的温暖与善意……
——常芳的《河图》,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用大家族命运凸显世界性景观。
——吕铮的《打击队》,跳出类型小说的窠臼写出了更深层的文学性:每个人虽都不是完人,但他们性格的弱点并不影响其整体上人性的光辉。
——萧耳的《林中空地》,以一高档小区内名为“林中空地”读书会为媒,通过共读《局外人》《喧哗与骚动》《变形记》等名著,试图从中寻得对抗荒诞世界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也逐渐熟络起来,彼此帮助,走出各自生活的怪圈,实现个人意识的觉醒。
——周婉京的《造房子的人》,采用“虚”“实”相间的章节结构,每一章对应主要建筑“东方剧场”的一个部分;环形的叙事使首尾相互呼应,并将章节间的“留白”置于想象的空间,“造”出了一幢特色卓然的个性之屋。
四
以上限于本人阅读的信手拈来,无论是曾经“茅奖”作家的自我拓展,还是更多中青年作家新作的百花绽放,面对此情此景,的确很难再说存有所谓“大年”与“小年”之别。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消弭的背后体现出的则是一种逐渐强大的自信。
“茅奖”固然是标杆、是荣誉,但终究只是其一,而其一之外的天地同样广阔。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创作自信的观念与意识之呈现与强化,特别是行为上的切实跟进,确是更值得令人欣慰与祝贺的大幸事。
迈出自信的步伐,走向自信的目标,远比一个奖项更加重要!
(作者为知名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