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梁 好
曾高飞常年在财经和文学领域笔耕不辍,他始终恪守“躺着思考,坐着写作,站着做人,跑着逐梦”,坚持“左手财经,右手文学,用作品说话”的信念。
在《前行的青春》里,曾高飞写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写活了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他笔下的仇晓梅、肖小燕、林婉儿、陆贵等青年,在成长中蜕变、在责任中觉醒,鲜活地勾勒出一代人的青春轨迹与青春底色。
《前行的青春》是一部充满爱和能量的作品:仇晓梅在镇汽车站捡到身患重病、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仇拾,出于善良,她将其带入校园一边求学,一边打工。而宿舍其他女生对小孩的顽皮很排斥,并由此引发种种矛盾;经济上的困窘迫使她在学业和养育孩子间艰难平衡,不得不在饭店推销酒水来养育仇拾。而后仇晓梅不幸染病离世,更是将命运的悲剧性推向高潮。曾高飞是个内心善良和充满悲悯情怀的人,他不忍直面苦难,而是通过爱与责任的书写赋予这部小说超越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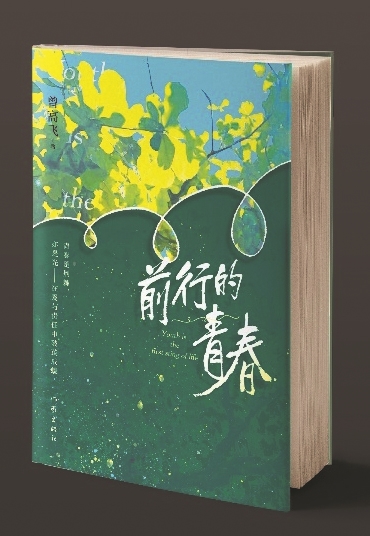
《前行的青春》,曾高飞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7月
仇晓梅对仇拾的爱与责任是生命对生命的救赎。仇拾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被亲生父母抛弃,使他变得自卑、敏感又脆弱;而仇晓梅的父母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双双离世,意外遭遇为她带来无法承受的生命之痛,失去至亲的她曾陷入绝望的深渊,甚至萌生轻生念头。两人都失去至亲至爱的人,成为同病相怜的孤儿。正是他们高度契合的人生命运和情感曲折,使得彼此情感互补、灵魂互通。“在父母去世后的那段日子,仇拾成了仇晓梅活下去的坚强理由和有力支撑……她跟仇拾同病相怜,同命相系,都成了孤儿。”仇拾也因为仇晓梅无微不至的照顾逐渐变得聪明、活泼、开朗起来,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改掉了以往的毛病。仇晓梅在自己人生最低落、情感最脆弱的状态下,却将仇拾领向一条充满温情和希望的道路。因为人性本能的情感需求和善良驱使,弥补了他们的情感和精神空虚,从而相互照亮,彼此温暖。
从《小镇青年》中乡村青年的命运抗争,到《前行的青春》里都市青年的精神突围,曾高飞始终关注个体在困境中的成长可能性。小说以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和自我实现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书写他们即使深陷困境却仍然向上向善、坚毅奋进,给人带来精神曙光。
除仇晓梅之外,520宿舍其他三位女生贺怡、肖小燕、林婉儿最初对仇拾充满反感和厌恶,然而当她们得知仇拾是被遗弃的孤儿并身患重病时,怜悯油然而生并主动加入照顾仇拾的行列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学会了关心他人、承担责任,逐渐褪去了当初身上的稚气。
同样,1314宿舍的曾枭、陆贵等男生,在与仇拾接触中,也经历了成长的蜕变。曾枭起初对仇晓梅和仇拾的事情并不了解,但在与仇拾相处中被其天真可爱所打动,逐渐对这个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陆贵因照片风波而训斥仇拾时,曾枭为维护仇拾,与陆贵发生肢体冲突。看似简单的矛盾纠纷,事实上是曾枭内心对正义和责任的坚守。仇晓梅去世后,他主动接过抚养仇拾的重任,并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子汉。而陆贵在经历此次事件后,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从冲动鲁莽逐渐变得成熟稳重。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面对生命中的种种磨难时,也经历了内心的成长与蜕变,实现了从稚嫩到成熟的跨越,从脆弱到坚强的升华,凸显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个大的变动、充满主体意志和不同想象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碰撞、命运和人生境遇的变化,也一定会在爱情的场域有所反应。仇晓梅与曾枭始于陌路、终于生死的爱情羁绊;陆贵与肖小燕的爱情,是在相互支持中不断成长,他们相约一个保家卫国,一个回乡创业,展现出当代年轻人对爱情与责任的理解;而贺怡与方明的爱情则充满波折与考验。贺怡因为经济上的困窘,在面对爱情时小心翼翼,她努力偿还债务,为的是能够平等地站在方明面前,这是对爱情的慎重和坚守。
小说在青春叙事中还融入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小说最后,仇晓梅的去世,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创伤的缩影。真实可感的细节描写,将青春叙事融入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又赋予小说纪录片的质感。但曾高飞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苦难描写,而是在困难中书写人性的光芒:仇晓梅不幸染病后,大家对仇拾尽力照拂,以及为仇晓梅和曾枭举办线上婚礼,都彰显着青年群体在困难面前的温情与凝聚力。
小说中的时代性还体现在青年的认知更迭中:肖小燕毕业选择回乡承包山林水库,既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响应,也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对“故乡”概念的重新定义:他们不再将城市视为唯一的梦想之地,而是在城乡融合中寻找发展机遇,这种新视角突破了传统青春文学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展现出Z世代青年具有前瞻性的时代认知。这与曾高飞另一作品《小镇青年》中的张美生形成呼应。《小镇青年》是新世纪初乡村青年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主动突围,《前行的青春》则是新时代青年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价值回归,两组不同时代的人物凸显出作者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产生时空交错的恍惚。那些关于宿舍矛盾、学业压力、求职焦虑的描写,既是对特定年代的真实记录,也暗含着超越时代的青春本质。正如曾高飞在自序中说:“窃以为‘前行’二字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也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人生态度……‘前行’既是我们生命的内在需求,又是一代代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他反复提及的“前行”二字,不仅是小说主人公们穿越困境的生命姿态,更是一所大学、一座城市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写照。仇晓梅的离去并非故事的终点,而是精神的延续——曾枭接过抚养仇拾的责任,贺怡与方明投身大西北建设,陆贵成为保家卫国的飞行员,这些未完待续的故事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青春的价值不在于完美的结局,而在于永远向前的勇气。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

1月28日,国网宝鸡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秦岭输电运维班成员赵鹤在变电站张贴新春对联。陕西省宝鸡市凤县的秦岭深处坐落着一座特殊的“融冰”电站——110千伏秦岭融冰变电站。由于当地处在冷暖气流交汇带,雨雪天气极易导致输电线路覆冰。
1月30日,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北集坡街道组织的“品书香 赏非遗逛大集”活动热闹开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和便民服务项目吸引周边村镇居民前来逛大集办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