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 焦文宁
在西方文化中,“巴别塔”象征着傲慢和混乱。相传,求名心切的人类意欲修造巨塔以求登天,引发神怒。于是,神从中作梗搞乱人的语言,使人“各说各话”无法合作,修塔就此不了了之。若从“巴别塔”的隐喻观之,文明的进步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集合个体禀赋形成集体智慧,不断驯服混乱,修造各式“巴别塔”的历史。而在形形色色的文明成就中,百科全书凭借对知识的整体性追求,试图成为“统一性和正确性的坚实堡垒”,俨然就是“知识的巴别塔”。正因为这种独特且重要的地位,这座巨塔便有了多重身份:诱人的智慧之果、一门出版生意、知识的生产传播系统、观念战争的必争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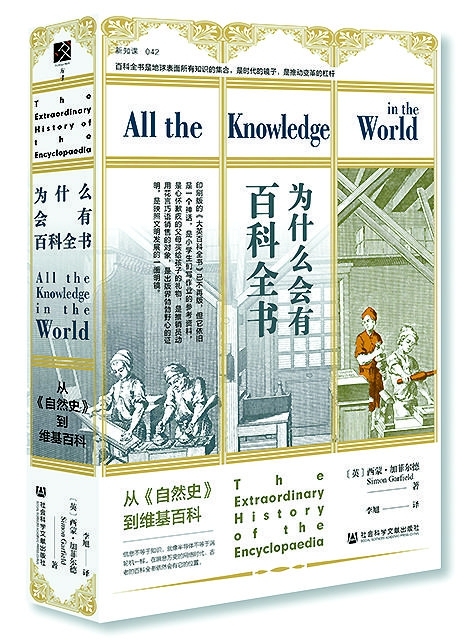
《为什么会有百科全书:从〈自然史〉到维基百科》[英]西蒙·加菲尔德 著 李旭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出版
作者加菲尔德是数字时代里少见的纸质百科全书爱好者和收藏者,在《为什么会有百科全书》中,他以轻快的笔触,带领我们回望了百科全书在过去2000年里的历史嬗变:从公元77年普林尼写作的用于“全面教育”的《自然史》,到近代身兼教育工具、研究参考和身份象征数职的《大英百科全书》,再到今天全球共建、点击即达的在线百科。但作者的重点显然不在于告诉我们历史上究竟有多少种百科全书。真正有趣和重要的是,作为知识的“集散地”,只要看看百科全书的历史面相,就能快速把握特定社会乃至整个时代的知识理解,洞悉知识的社会效应与生产传播方式。作者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可以说,本书属于典型的“知识社会史”研究,即抓住知识与社会的历史联动,使两者相互映照、相互说明,最终产生四两拨千斤的解释力度。
要理解这种联动关系,就不能不谈及作者对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考察。正是在这一时期,百科全书迎来编撰思路上的革命性转变,同时升格为时代精神的公共载体。彼时,一批“最强大脑”以罕见的博学和热情投入到词条撰写中,形成了以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等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经启蒙学者之手,这部划时代的《百科全书》明确将理性、科学与批判精神作为识别和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于是我们便看到,经过大规模协作和系统性分类,人类心智的全部成果被整齐有序地排布在一棵“囊括所有科学与技艺的谱系树”上,各枝干从记忆(历史)、理智(人文与自然科学)、想象(诗歌)三大主干分出,从形而上学到机械、艺术的一切领域被一网打尽。而与这种做法相对的是,此前的百科全书还主要是“条目定义书”或“信息存储库”。对比之下,法国《百科全书》的成就不可谓不壮观。
从编撰思路的转变,不难体味到彼时欧洲那种自信昂扬的精神气质。在理性和科学进步的支撑下,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以气吞山河的姿态,试图征服知识的海洋。如狄德罗所言:“百科全书的目的是汇集散落在地球表面的所有知识,向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展示知识的通用体系……我们的后代会因此变得更博学,进而变得更有德性、更幸福。”运笔至此,作者表现出了他的批判性。他提醒读者们去质疑,这里的“我们”说的是“欧洲的我们”,还是恰如百科全书追求的知识所应有的普遍性那样,是“全人类的我们”;读者也应当怀疑,《百科全书》之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到底是要“展示”知识,还是在“强加”权力。因为就在走出书房后,《百科全书》的主要订购者们——新兴的英法资产阶级——也以气吞山河的姿态,“正准备开启规模庞大的殖民战争”。由此可见,一定的知识实践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现实若合符节,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被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现实所滋养,也反哺了那个时代的自信与自负(书中指出,这种自负在1911年的第11版《大英百科全书》中才烟消云散)。而在欧洲社会内部,各式百科全书不仅是学者案头的参考书,更是公共舆论的催化剂。编纂者们有意将批判性的观点埋藏在各类条目中,使它们在读者心中慢慢发酵。读者在翻阅条目时,不仅会接触到对工艺与技术的礼赞,也会接触到对君主专制的暗讽、对宗教教条的质疑。于是,这座“知识的巴别塔”在表面上是知识宝库,在隐秘处其实是挑战旧时代的思想碉堡。在那个人类对信息大爆炸还没有多少应对经验的年代,百科全书及其编者群矗立于信息洪流之中,成为最有权威和号召力的领袖。因此,作者反复指出百科全书的复杂性:一方面,它以求知为宗旨,本应力求中立和客观;但另一方面,它又被打上编者和时代的烙印。每一版百科全书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无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
总而言之,百科全书扎根于时代观念、权力结构和技术条件等构成的交汇地带中,其复杂性和历史局限性源于自身这种无可避免的社会嵌入性。但在复杂性和局限性之外,历史回望所道出的更深层的东西却很单纯:纵使百科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但人类面对复杂世界时表现出的勇气、团结和求知欲从未有变,这是百科全书不变的精神底色。也正因此,或许人类自己都不会乐见“知识的巴别塔”的建成——只有未完,才可待续。恰如爱因斯坦所言,“追求真理和美,是让人永葆青春的秘诀”。
最后,在人工智能发展呈摧枯拉朽之势的当下,我忍不住想接续作者并邀请读者探讨两个延伸性问题。第一,本书的历史回望止步于在线百科,但在线百科果真就是百科全书的最新形式吗?透过全书的介绍,可以深刻地意识到,百科全书绝不简简单单地是一种四四方方、可感可见的“物体”,在根本上,百科全书是一个“集合”,是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获取的特定实现方式,涵盖人类智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一来,是否可以进一步把大语言模型及更广义的人工智能视为百科全书的新存在形式?应当怎样续写百科全书的历史?第二,透过百科全书的历史演化可以看到,人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总体发展规律是不断大众化,而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新近出现的还有加速的黑箱化和去中心化——知识的“第一作者”更难追踪甚或出自“非人”,如此一来,也就谈不上回溯知识实践的完整过程。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对于读者、作者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言,这些新动向又意味着什么?我想,在读罢《为什么会有百科全书》这一历史学研究之后,更多关于“百科全书”的未来学思考正当其时。

1月28日,国网宝鸡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秦岭输电运维班成员赵鹤在变电站张贴新春对联。陕西省宝鸡市凤县的秦岭深处坐落着一座特殊的“融冰”电站——110千伏秦岭融冰变电站。由于当地处在冷暖气流交汇带,雨雪天气极易导致输电线路覆冰。
1月30日,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北集坡街道组织的“品书香 赏非遗逛大集”活动热闹开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和便民服务项目吸引周边村镇居民前来逛大集办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