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海 飞
收到样书的时候,我开始想念那座住在我身体里多年的县城。我常常觉得,县城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朋友。1992年,我退伍回到浙江诸暨,从火车站下车,看到了右侧的西施商场,听到了张学友和叶倩文轮番上场的歌声,年轻人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服装,留着郭富城发型,我几乎是在一瞬间,像一滴水融进大海一样,融进了县城。
我在化肥厂拉过煤,在夜市摆过摊,在报社写过稿。那时候我很快乐,虽然钱不多,但够去小乐园喝一碗冰镇绿豆汤,够买一张三块钱的海浪歌舞厅门票,够在诸暨剧院看一场诸暨市越剧团演出的《西施断缆》。后来我离开县城,去往省城杭州编杂志、写小说,生活渐渐安稳。可安稳有时候像一层雾,让你看不清自己从哪儿来。直到有一天,我在穿衣镜前,像时光穿越一般看见自己还站在县城的一条街上,年轻,懵懂,四下张望。那一刻我终于知道,我从未真正离开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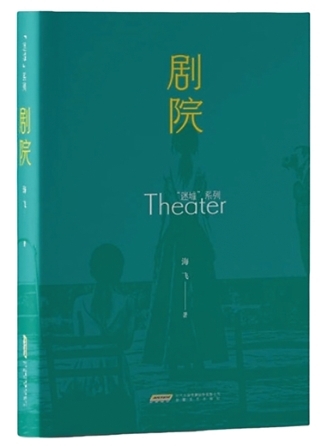
《剧院》:海飞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于是,我开始写长篇小说《剧院》。写的是一个叫陈东村的警察和一个叫迟云的越剧演员的故事,他们一个想要从派出所回到刑警队工作,一个想要演艺事业登上新高度,这是他们的执念。同时有执念的是,汤宝琴想要女儿出人头地,焦聪明想要好好经营照相馆,老裘想要发财后回到剧团工作……如此等等,无比琐碎却又热辣新鲜。小说还写了一个由诸暨、嵊州和上虞这三个地方拼凑虚构而成的南风县,写1998年到2003年的5年间,写一个只有母亲和两个女儿的家庭,写一桩案件,写疼痛与挣扎。但我真正想写的,其实是那片土地上拥挤、嘈杂、鲜活的人间。2003年底,我辞职离开报社。此后5年中,我的生活不停变化,如同小说《剧院》中的5年,各色人等的命运也有着各样的反转。我其实热爱着县城的烟火气,觉得它比大城市多了一些熟人社会的羁绊,同时也多了一层熟人社会的温情。
有人说,《剧院》不像典型的悬疑小说,更像是世情小说。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真正写下的不是类型,而是记忆。是那些在太平桥、人民路、横街、老鹰山下发生过,又随风飘散的生活,是我在县城储存下的所有声音、气味和温度。
每一次写县城的街巷、剧院、江水,我都像是在和过去那个穿着劳动皮鞋、略显困顿的青年对话,然后得到治愈。就像我在小说题记中写下的,我们都置身剧院,却难以看清剧情的走向。在社会这座大剧院,我们每个人有时是演员,有时是观众。而县城,就是我最初登场的那座剧院。它教我哭笑,教我行走,也教我写下第一行字,第一部作品。
中国有千余座县城,曾有过数千座县城影剧院,而生活在县城的,更是庞大的人群。我与县城,从身居其中,到后来远远观望。现在我老家的村庄已经拆迁,在县城生活时的街道变了模样,影剧院也早已成了一家超市,连当年卖包子的“桃花源”也找不到了。可它们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我怀念它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写它——写下它的气味、它的温度、它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悲欢。最终写下的,就是热气腾腾的《剧院》。
如果你也曾在某个县城生活过、离开过、又梦回过——那么在小说《剧院》里,也许和陈东村以及迟云一样,有你的一个座位。我们都在各自的剧场里,演过青春,也演过受伤;演过拥有,也演过离别。而所有的故事,最终当我们回望时,我们才真正拥有它。
